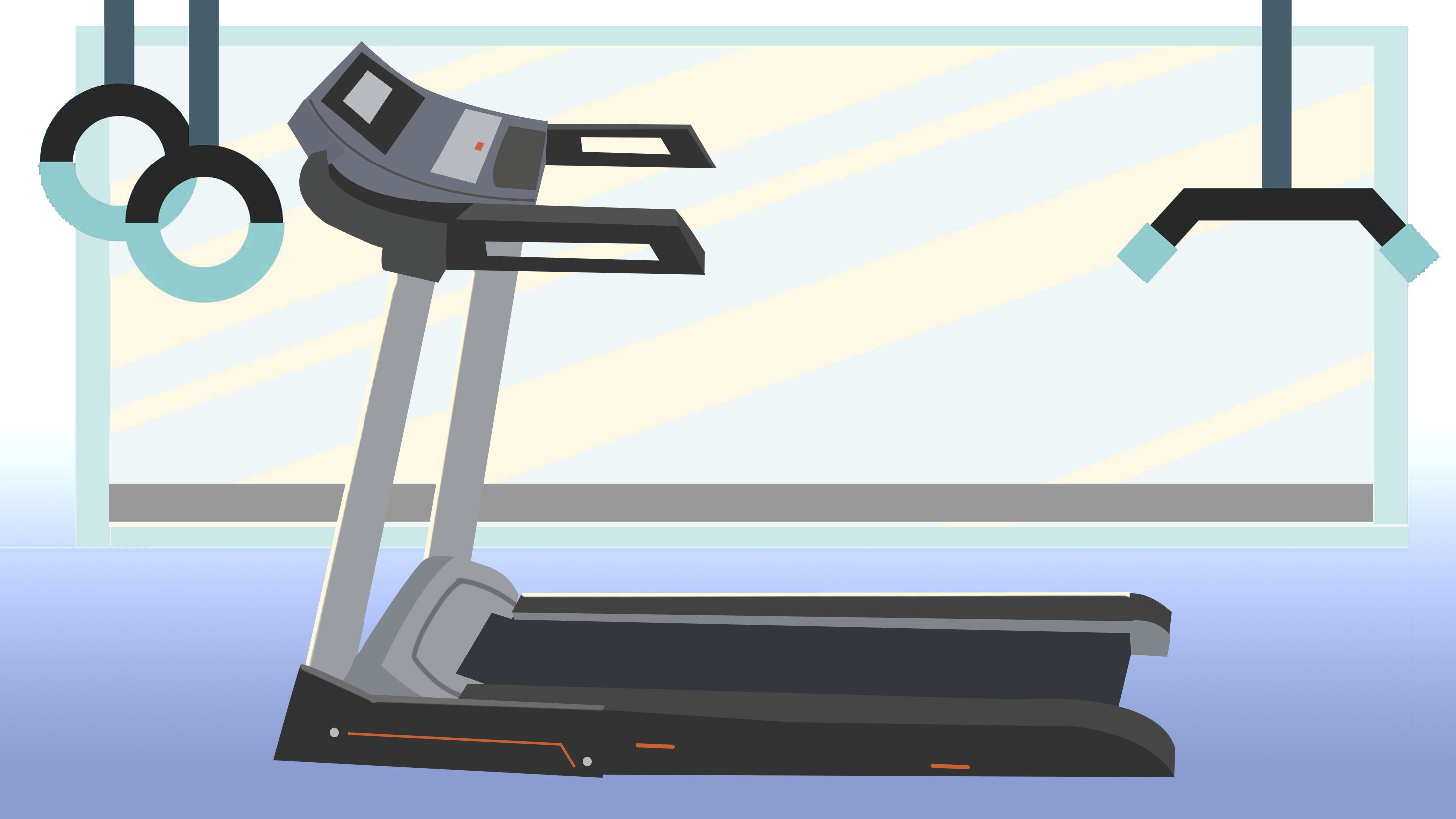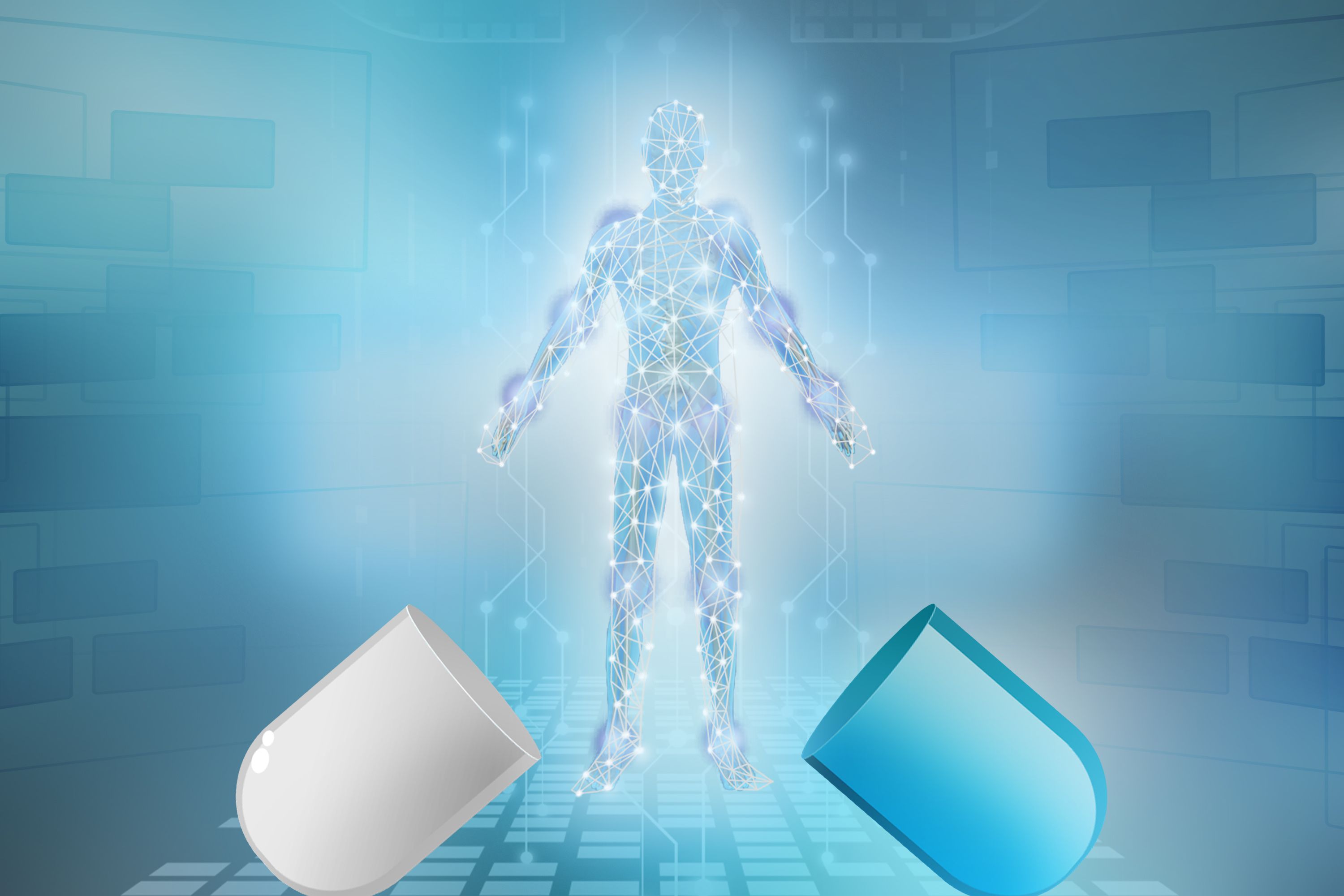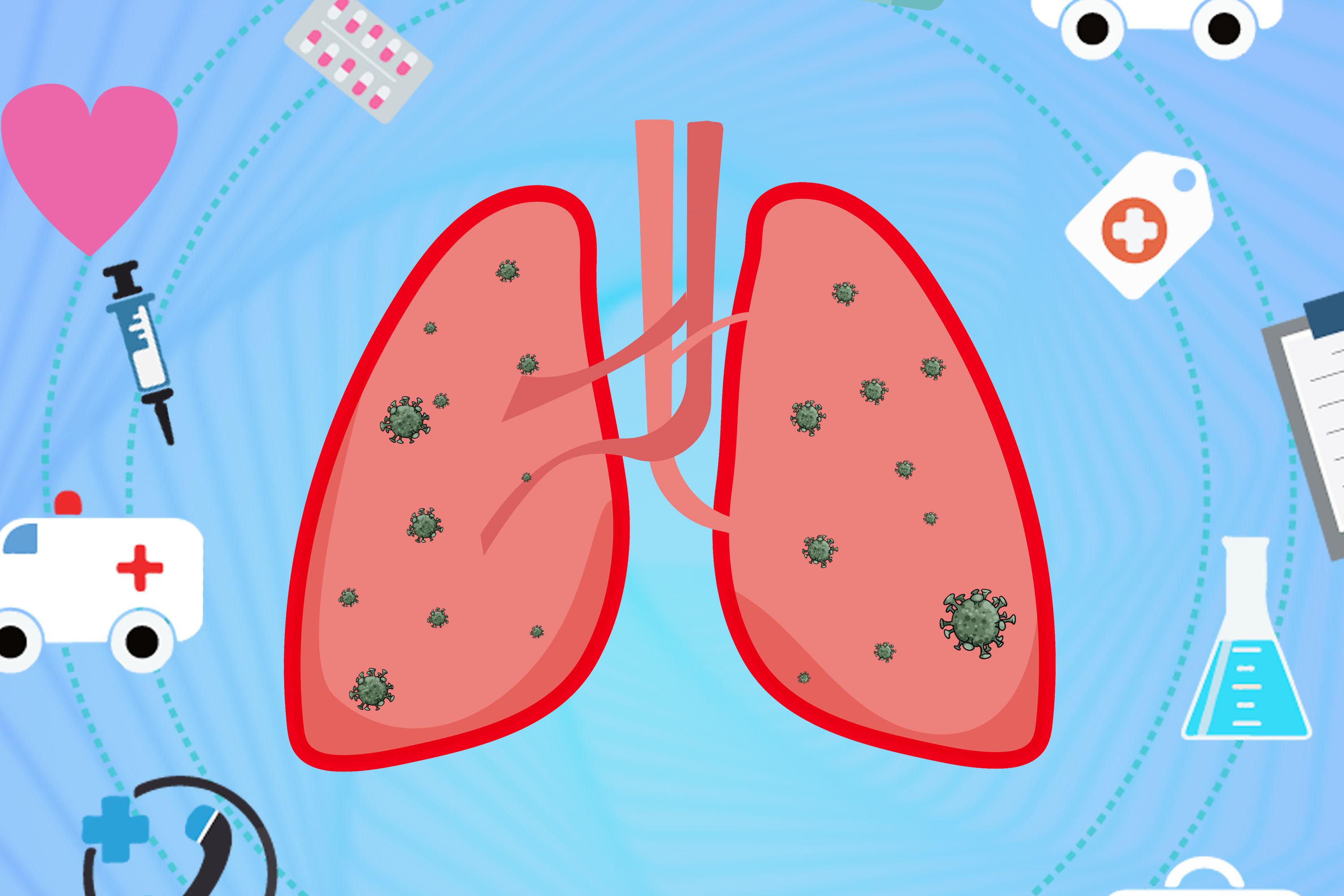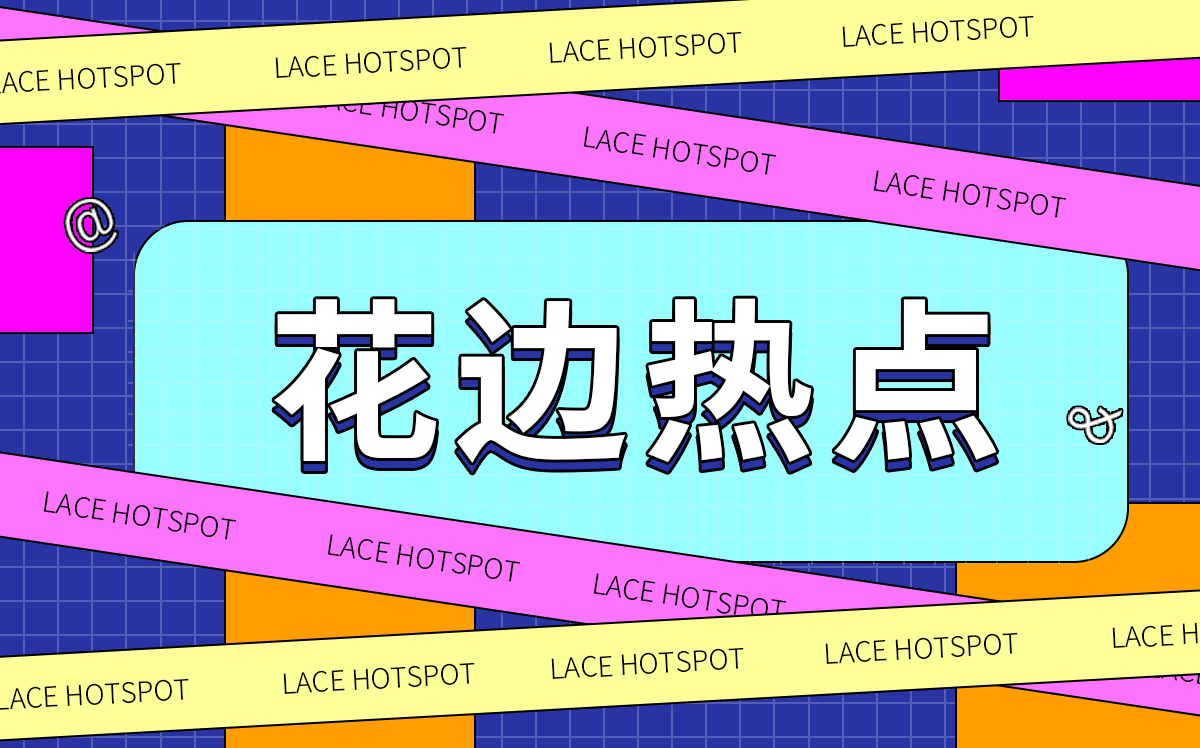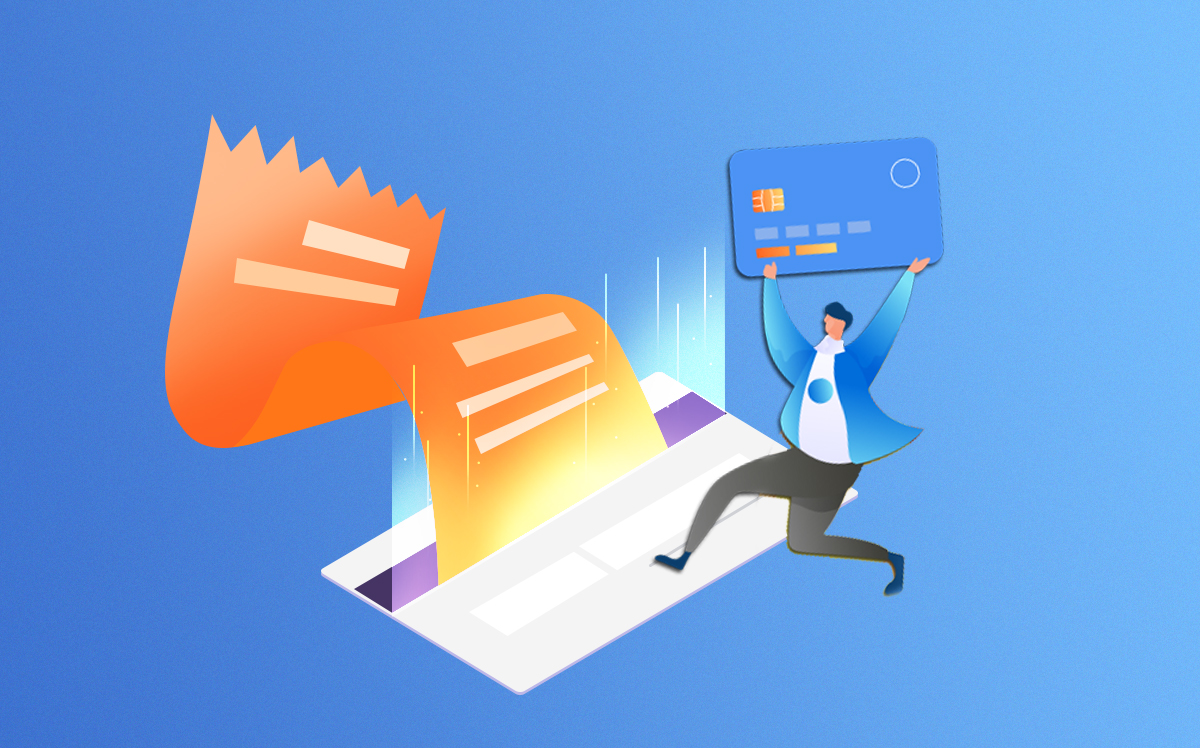巴以冲突、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多年以来,中东地区始终在国际新闻“热点”里占有一席之地。这块土地何以如此命运多舛?昝涛所著的《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或许会给读者一些启示。
就像书名里的“历史视野”显示的那样,作者讲到了不少国人感觉有些陌生的“冷知识”。譬如,如今一说到伊斯兰教内部对立,往往将伊朗作为“什叶派”的大本营。但书中就提到,伊斯兰教传入如今的伊朗地区已有1300多年历史,而“什叶派”独大则是公元16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波斯人大多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萨非王朝(1501-1736)建立后,立即“宣布将十二伊玛目派尊为官方宗教,实行强制皈依的政策,并在钱币上铸上什叶派的口号”。其实萨非王朝治下并没有多少非穆斯林居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萨非王朝的东、西两侧,有着两个信仰逊尼派的强国——(中亚的)乌兹别克汗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结果,“萨非王朝将什叶派宗教学者纳入王朝的官方体系。官方的什叶派宗教学说则赋予了国王神圣的外衣,巩固了国王的权力,并成为与乌兹别克人和奥斯曼人进行斗争的意识形态武器”。
但本书并无意像菲利浦·希提的《阿拉伯通史》那样,全面阐述中东的久远历史,而更多着眼于“伊斯兰世界”对西欧势力东渐的回应。甚至连“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本身,也来自作为域外的西欧。就像书中所指出的,“‘伊斯兰世界’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被笼统使用的概念”。仔细想来,的确如此。在近代的欧洲,“穆斯林”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两个概念几乎画上等号。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设在欧洲(伊斯坦布尔暨君士坦丁堡),辖下半数居民是基督徒,它的海军、外交等也很倚重基督徒……这真的可以算作“伊斯兰世界”吗?若是以统治者的信仰划界,更极端的情况就会出现在莫卧儿帝国(1526-1857)统治下的印度,将印度教徒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整个次大陆算作“伊斯兰世界”,似乎更加荒谬了。
 (资料图)
(资料图)
于是,作者对“伊斯兰世界”的来源进行了梳理。根据书中的描述,由于十字军时代以来的政治对立,西方力图塑造一个对立面,去确立欧洲的正面性。后世的“东方学家”也深受这个传统的影响:欧洲无疑是正面的,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就是其对立面。“‘伊斯兰世界’是西方在长期面对伊斯兰扩张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个‘他者’。”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实中的整个世界都不惮使用这个“西方强加给全世界的定义和观念”呢?这是因为,“从反抗者的角度来说,接受这个概念时,也会逐渐意识到其原有的负面内涵,从而作为反抗者来重新定义它,并赋予其正面的意义和属性”,这样“才能号召他们所想象的那个范围广阔的穆斯林共同体——也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去自强或反抗”。因此,“作为接受方的伊斯兰主义者,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接纳了这一被西方强加的概念标签,又使其成为反西方意识形态的基础”。
即便如此,接纳他人创造的概念终究有几丝悲哀。“中东”(这也是个基于西欧本位的概念)有着悠久的文明史,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倒有两个在此(古埃及、古两河流域),近世遭遇的衰弱与殖民,更是一种淤积在胸的伤痛,或者用《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书中所用的概念,叫作“呼愁”。
这是土耳其出身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所用的词汇,以表述因“过去的荣耀和现实的灰暗”之间的强烈反差所造成的“一种介于肉体痛苦与悲伤忧虑之间的感觉”。帕慕克说“呼愁”是伊斯坦布尔的精神特质之一,这座城市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往(东罗马的千年帝都),而如今它既失去了历史上那种高度的荣耀,也失去了“本我”,但随处可见历史的遗迹和废墟,又在提醒人们再也难以恢复的过去荣光。其实,在西方强势笼罩下的现代“伊斯兰世界”,又何尝不能用这个最早出现在《古兰经》里的词来形容呢?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一书将中东分为三大区域: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与伊朗(波斯)。这恰好也是当代中东人口最多的三大族群。同样面对西欧崛起,强弱异位造成的“呼愁”,三者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
相比土耳其与伊朗,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是一个显著的特征。而在作者看来,这倒反而是历史的“常态”——中世纪阿拉伯人短暂君临中东才是例外。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北移到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人也是分而治之的。西方人更不会再允许中东这个地缘位置如此重要的地区出现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种种内外因素,使得处于中东核心地带的阿拉伯社会至今仍然是碎片化的、分裂的,短期内,也看不到重构之可能。”
这样一个碎片化的阿拉伯世界在21世纪初期进一步遭遇了挫折。书中引用了马克思·韦伯的论断,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合法统治形式建立在三种基础之上:理性(法律)的基础、传统的基础与卡里斯马(charisma)的基础——对具有超凡魅力人物的服从。当代的阿拉伯国家尽管也在表面上有成文的法律与官僚体系,但实质仍旧停留在“卡里斯马”的强人统治基础上。当萨达姆(伊拉克)、穆巴拉克(埃及)这样的强人倒台后,国家只能陷入长期乱局。于是,在这些“曾经的阿拉伯强国相继衰落之后,阿拉伯世界陷入碎片化与重重危机,阿拉伯民族所主导的中间板块阿拉伯半岛以及南部板块北非,都处于下降状态”。
因此,“冷战后,从地区性大国博弈的角度来说,土耳其和伊朗各自构成一极”。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历史上波斯萨非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竞争的时代。自面对西方崛起之挑战起,围绕如何实现复兴与富强从而走出“呼愁”心态,穆斯林精英大致有两种思潮:一是西方化的世俗主义;二是不同形式的伊斯兰主义。有趣的是,作为昔日两大帝国的后继者,当代的伊朗与土耳其在这两种路线里恰是各择其一。
谈到伊朗,书中有个非常贴切的论断:“在很多人眼中(大概是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伊朗被视为一个‘不正常国家’。”诚然,神权统治,似乎的确不太“正常”。但作者揭示了经历“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的另一面:它有选举产生的议会、总统,可在其之上还有“最高领袖”。最高领袖由专家会议选举产生,专家会议可在领袖不称职或失去担任领袖的必要条件时废黜领袖。反过来,专家会议所有候选人必须通过宗教考试,获得保卫者委员会批准,才有竞选资格,而保卫者委员会成员却是由最高领袖任命的。从作者的这些描述看,这个互相制衡且复杂的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本身就需要理性,而与“宗教狂热”风马牛不相及。用作者的话来说,“伊朗这种复杂的政治体制,恰恰是伊斯兰主义与现代主义妥协的产物,体现出伊斯兰主义政治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调适”。
总而言之,“伊朗是被西方过度污名化了的国家。它在体制上的摸索和创新,尚未被充分严肃地对待和讨论”——当然本书的相关讨论也是浅尝辄止,不能不说是件憾事。相比伊朗,书中关于土耳其的篇幅显然多一些,这可能与作者自身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黑海-中亚中心”访问学者、土耳其博斯普鲁斯大学历史系访问研究员)。
如果说,伊朗的政体是伊斯兰主义向现代主义妥协的话,土耳其恰好相反,是世俗主义在逐渐回归伊斯兰。“在凯末尔党人看来,这世界上只有一种优秀的文明,那就是当时的欧洲文明,土耳其人需要做的就是达到当时欧洲文明的高度。”
建国之初凯末尔主导的激进改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治维新的时期的日本:土耳其人规定男人不能留胡子,要戴西式礼帽,日本同样也规定男人不能留发髻,天皇也穿起了西服……但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日本在继续西化,日语里用片假名直接拼写的外来词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而土耳其似乎却在走回头路,回归凯末尔曾经想极力抹去的“传统”。
在这方面,前几年有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博物馆(原来是教堂,后来改成清真寺)又被埃尔多安当局改回了清真寺。此举引来了很多批评,很多人认为,这是土耳其长期坚持的世俗主义的一大倒退。
但《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给出了不一样的见解。在作者眼中,“恢复清真寺的理由,应该主要不是来自宗教本身,因为有人计算过,伊斯坦布尔根本就不缺清真寺,圣索菲亚博物馆对面的蓝色清真寺根本没有多少人去做礼拜”。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说,恢复清真寺代表的就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所欲保留的那个历史记忆,也就是土耳其/穆斯林相对于西方/基督徒的胜利(1453年灭亡东罗马帝国)。对这种胜利的招魂和纪念,其实是埃尔多安服务当下土耳其国内的权力政治的精密算计。
但博物馆改成清真寺本身,毕竟是伊斯兰压倒世俗主义的一个象征。以此看来,土耳其与伊朗正在似乎走向“殊途同归”之路。就像作者所说,“土耳其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在现代主义面前达成妥协,这是一条‘土耳其道路’”。这条路能不能安稳地走下去呢?还不得而知。毕竟作者也承认“土耳其的困境在于,它的政治建立在一个价值分裂的社会之上”。但至少在如今这个时代,土耳其在中东大变局里可以算作一个成功者——“作为中东的北方板块,土耳其和伊朗长期居于优势地位,尤其是土耳其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
“优势地位”这样的描述,让人想起了以色列的存在。书中对以色列着墨不多。当然,以色列不属于“伊斯兰世界”,其体量也不能与土耳其、伊朗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它的确是中东地缘政治棋局里的一个重要棋手。更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是一个建立在犹太教基础上的世俗国家。为什么在阿拉伯世界,“各种世俗主义因其外来性而在当地难以‘接地气’,从而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从外面贩卖来的各种济世方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以色列却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所引出的另一个话题了。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昝涛 著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2022年5月版